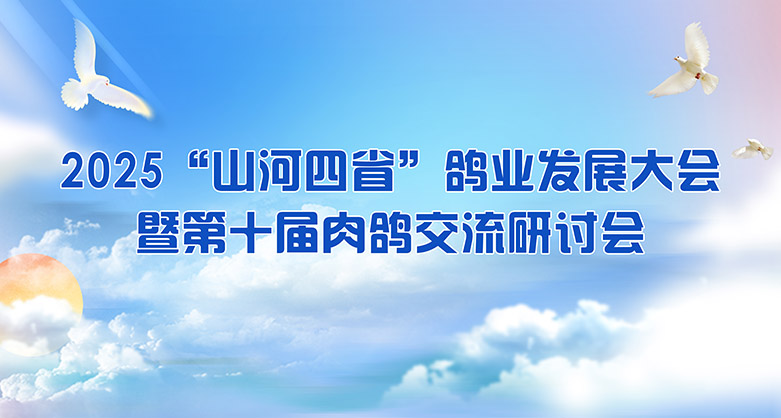2021版《動物防疫法》解讀一:修訂的主要背景
2021年1月22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動物防疫》修訂草案,隨即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69號主席令》形式公布,自5月1日起實施。這是時隔13年的再次系統性修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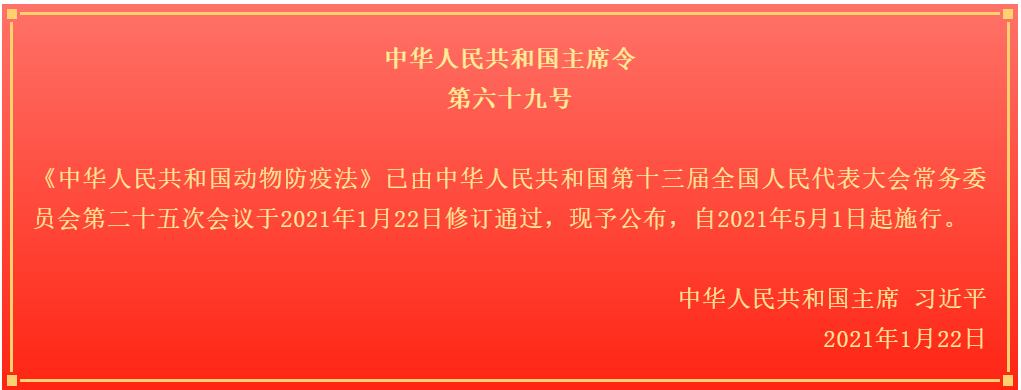
動物防疫法可以稱之為我國動物防疫工作的“母法”,動物防疫和獸醫人員管理的法律制度均由該法確立,本次修訂還專門授權國務院制定獸藥、獸醫器械管理辦法,其在獸醫領域的“基本法”地位更加突出。

筆者長期關注動物防疫和獸醫管理工作,曾參與相關法律法規修訂研討,計劃利用6至8篇的篇幅,在與上版防疫法文本對照基礎上,對2021版《動物防疫法》作簡要解讀。
系列解讀一:
《動物防疫法》修訂的主要背景
一、宏觀背景
熟悉動物防疫工作特別是法律制度演進的讀者都清楚,動物防疫法的前身是國務院于1985年發布實施的《家畜家禽防疫條例》。長期以來,社會上有很多聲音質疑《動物防疫法》沒有得到全面貫徹落實,在野生動物、水生動物、寵物的監管上存在缺失。
其實,從《家畜家禽防疫條例》到《動物防疫法》的立法變遷,是解釋、理解上述情況的一把鑰匙。但這不是本文論述的重點。1997年,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動物防疫法》,動物防疫工作立法層次從行政法規上升為法律;2007年,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對動物防疫法第一次修訂,后歷經2013年、2015年兩次修正,本次是對動物防疫法的第二次修訂。
每一次法律修訂或者修正,都有其誘因或背景。
2007年第一次修訂,最大的背景是2004年的高致病性禽流感阻擊戰和隨之而來的2005年國務院發布的《關于推進獸醫管理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這次重大動物疫情防控實踐以及國務院文件的出臺,確立了行政管理、監督執法和技術支撐“三駕馬車”的動物防疫機構設置框架,國務院和省市縣三級地方人民政府均設立了獸醫主管部門,縣級獸醫主管部門可以向鄉鎮派駐站點、人員,在鄉村建立村級動物防疫員隊伍具體承擔強制免疫注射工作,這些都在2007年修訂時吸收到法律規定中。
第一次修訂的《動物防疫法》于2008年實施后,全國動物防疫工作得到加強,法律在保障養殖業生產安全和公共衛生安全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近年來,我國畜牧業轉型升級的步伐不斷加快,生產組織方式和經營模式創新發展,對動物防疫工作的要求逐步提高;飼養畜禽和消費畜禽產品的體量持續攀升,生豬常年飼養量達到10億頭(存欄+出欄),占全球一半,肉類和禽蛋產量穩居世界第一,而生產單元以分散的小規模飼養經營場戶為主體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改變,龐大的飼養規模與相對落后的生產方式之間的矛盾給動物防疫工作帶來了巨大壓力,對法律保障和支持力度的需求更加迫切。此外,境外重大動物疫情頻發,A型口蹄疫、小反芻獸疫、非洲豬瘟先后從境外傳入我國,牛結節性皮膚病疫情在部分邊境地區點狀散發,動物疫病防控形勢始終嚴峻。
鑒于上述形勢變化,以及距第一次修訂已有10年時間,國家立法機關注意到了《動物防疫法》修訂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于2018年9月將《動物防疫法》修訂列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這是本次修訂的宏觀背景。
二、四個具體背景
從修訂中重點完善和新確立的法律制度及規定來看,本次修法工作有四個具體背景,直接影響到法律條文的設計,可以歸納為“兩項改革、兩場疫情”。“兩項改革”,指政府機構改革和農業綜合行政執法改革;“兩場疫情”,指非洲豬瘟疫情和新冠肺炎疫情。
第一,關于政府機構改革。
以大部門制改革為主要表現形式,整合黨政機構職能,精簡機構設置,規范行政管理職能執行主體。在國務院層面成立農業農村部,原農業部內設機構畜牧業司和獸醫局合并為農業農村部畜牧獸醫局;在地方層面,原獨立或半獨立設置的畜牧獸醫局合并進農業農村廳,內設畜牧獸醫處室;在機構職能方面,行政管理職能全部劃入農業農村主管部門,很多地方檢疫與行政檢查等監督管理權限均納入農業農村部門“三定”方案。
上述情況對法律修訂影響的最直接表現,是將原法中“獸醫主管部門”修改為“農業農村主管部門”,動物衛生監督機構及其官方獸醫不再履行監督檢查等行政職能。
第二,關于農業綜合行政執法改革。
按照中辦、國辦印發的《關于深化農業綜合行政執法改革的指導意見》,將“分散在同級農業農村部門內設機構及所屬單位的行政處罰以及與行政處罰相關的行政檢查、行政強制職能剝離”,“整合組建農業綜合行政執法隊伍,由其集中行使,以農業農村部門的名義統一執法”。受這一改革影響最大和最直接的,就是動物衛生監督機構。
按照上一版《動物防疫法》規定,動物衛生監督機構為經法律授權、負責動物檢疫和防疫監管執法的機構,各地成立動物衛生監督所,雖大部分為事業單位性質,但可以依法開展行政許可(檢疫出證)和監管執法工作。
改革后,執法職能及相關編制被劃入農業綜合行政執法機構,檢疫和監管職能劃入農業農村部門,動物衛生監督所紛紛改為動物檢疫技術支撐單位,更名為動物衛生技術中心,或并入動物疫病預防控制中心等等。在法律修訂中,雖保留了對動物衛生監督機構作單獨表述,但已無法承擔動物防疫監管執法職能;而從各地機構改革的實際情況看,法律中的動物衛生監督機構已很難與動物衛生技術中心之類的技術性事業單位掛鉤,保留動物衛生監督系統及其機構、人員的努力更多只具有象征意義。
動物檢疫工作機制以及動物衛生監督機構和官方獸醫建設,應該成為下一步重點研究和破解的課題。
第三,關于非洲豬瘟疫情。
2018年8月,在遼寧報告發現第一起非洲豬瘟疫情,正式宣告了非洲豬瘟病毒攻克邊境管理,進入國內。很快,疫情短短數個月內遍布全境,暴發勢頭之猛,傳播速度之快,令人驚愕。疫情給廣大生豬養殖場戶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損失甚至災難,生豬產業哀鴻遍野,豬肉價格持續攀升,對社會經濟造成了一定影響。
從疫情發生后國務院和農業農村部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來看,國家層面力圖在短期內控制、消滅疫情的努力是應當肯定的。但是,部分地方動物防疫體系失靈,防疫隊伍能力嚴重不足,影響了防控措施的有效落實;非洲豬瘟帶來的損失和尚無疫苗可用的現實,也暴露了動物防疫工作鏈條不全、重預防不重根除的問題。
可以說,非洲豬瘟疫情是對本次法律修訂影響最大的一個背景。
第四,關于新冠肺炎疫情。
新冠肺炎疫情是在動物防疫法一審修訂草案已基本成熟的情況下突然暴發的,對修法工作也產生了重要影響。修法進程上,推遲了審議的時間;修改內容上,集中加強了關于維護公共衛生安全的規定。疫情發生后,全國人大常委會迅速通過《關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和濫食野生動物等行為;首次制定專項立法修法計劃,強化公共衛生法治保障,涵蓋約30部法律制修訂任務,《動物防疫法》作為這個專項計劃中規定完成的第一部法律,受到格外重視。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法律修訂后期大幅增加了關于防范人畜共患傳染病和加強野生動物防疫檢疫監管的內容。